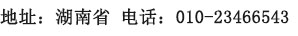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一天一夜。
石头旁有条毒蛇。
我不动,它便咬不着我。
忽然——
“当心,有蛇。”
有人好死不死地拍了我一把。
1
我从石头上摔了下去。
我还没来得及看清这煞星,就看见那蛇寻我而来。
我想逃。
腿麻了。
被咬了一口。
我绝望地躺在地上,既然已经中毒,那还跑什么。
可这四周又没了蛇的声响。
我转眸一看,是个特别好看的小公子。
公子生得俊朗,一袭白袍,举止儒雅,温润如玉。
我只从话本中知晓有这般模样的人,这还是第一次亲眼所见。
我住在山下,长在山中,见过的人,都是与泥相似的。
这样的小公子,不染尘泥,是会被蛇的模样吓哭的吧。
但他手里竟捏着那蛇七寸,拿出砍草药的弯刀,温柔地将蛇头割下。
如果不是看见蛇头落地,那举动儒雅地就似翻过一张书简。
好狠的心,好漂亮的脸。
我一时对他有些欣赏。
“这山林间怎会有如此剧毒的蛇,还是收了去,免得祸害弱小。”小公子喃喃半晌终于想起我,“啊,姑娘你被咬了。”
哈,谢谢您还记得我。
于是我阴差阳错,被这小公子捡了回去。
他说我一个小孩子落在山间,很可怜,他要给我解毒。
我回头看着掉落在山间的蛇头。
应当是小七最可怜。
山头这么大,它刚出去走走,就把命搭上了。
那是师父最喜欢的宠物小七,家养的,不似野物,少了些凶猛劲儿,以为人人捏七寸,都是师父宠爱的手。
可怜,可悲。
2
我师父是“天下第一毒王”,这是她自己取的名号。
她日复一日对我说,这天底下就没有她毒不死的人。
我那时年幼,当真对她崇拜得紧,喜得不行,她千挑万选收我为徒。
而后我长大些,便发现了她话里有逻辑错误。
首先,她就毒不死我。
难不成,我不算人?
师父捡到我时,喂了我一碗毒药,我活着,这激发了她的胜负欲。
想方设法将我毒死,成为了她人生追求的新目标。
为了方便,她便收我为徒,管我吃喝,教我些简单的毒理。
虽然我至今活着是她职业生涯的一大耻辱,但那些毒也会在我身体里帮她折腾我,惹得我难受。
其次,师父的毒,总会被另一人所解,那人被称为医仙。
这种事儿师父从不告诉我,会少了威信。
但我有耳朵,来来往往的风言风语,说我师父毒技不精,买主买回去毒人,竟被山上医仙解了去,大吵大闹在我师父门前,嚷嚷着退钱。
我都听得见。
况且这种事时常发生。
即使我师父精益求精,废寝忘食,制毒,拿我试毒,售毒,根据用户反馈处理售后,继续精益求精。
她契而不舍的精神,愈发高超的毒技,深入人心,顾客愈多,每当新品上架,都会一扫而空。
但那医仙还是次次解了她的毒。
周而复始,像个循环,我都有些疲惫了。
她再端药来给我,我都劝她:“师父不妨看开些,毒不死人不丢人。”
她感到被我羞辱,气得将我的嘴撬开,咕嘟嘟给我灌下去。
又给我擦擦嘴,教育我:“你穿这衣服,吃我粮米,都是凭空变出来的?那是卖毒换来的钱,这世上干什么都要钱。如今的客人越来越刁钻,我不进步,就会被淘汰,到时候你我二人就是穷光蛋。”
师父说的话深深激励着我。
我从那时起便想着,往后长大,我定要成为如师父一般有能力会赚钱的女人。
于是我从小事做起,一步一个脚印,从最简陋的毒融入果子,诱惑贪嘴鸟儿。
后来我发现鸟大多都是从山上来的,我便早起贪黑爬山捕鸟,让毒果子洒满山野。
有一只鸟的颜色很独特,在山间只瞧见过一次。
我亲眼看见它吃了我的果,可没过几天,我又在山里瞧见了它。
它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,小家伙,你可是第一只没被我毒死的鸟。
后来我将它捕了,拔了它的羽毛,做成羽毛毽,拔下它的喙,它的喙长且坚硬,能戳死毒虫,剩下的肉,我烤了。
我将烤好的鸟肉先分食给师父,师父破例那日没给我一碗她新制的毒药,而是交给我了一个玉佩。
她说这玉佩内是慢性的毒,虽不能直接致死,但不易被察觉,发觉便已是死亡之时。
于是,我一生要强的师父将我和小七派了出去。
小七咬我,我找医仙,医仙救我,我毒医仙。
师父的思路发生改变,她的人生也豁然开朗。
她不需要和那老头争什么天下第一毒天下第一医了,她只需要毒死医仙,便够了。
我离去时,师父说:“你将这玉佩赠予那老头,守在那老头身旁,他没死,你就别回来。”
我问:“这毒多久能毒死人?”
师父说:“十来年。”
医仙是个老头,那许是生老病死都捱不过十年。
我有疑惑,刚想开口,师父便打断我:“要小七咬了你,我把你扔过去?”
我赶紧带着小七的草笼上路。
我虽然不会死。
但小七咬人,特别疼,那是我从生下来至此,觉得最疼。
我便在医仙住所旁不远处,找了块大石头,坐在石头上,放了小七。
“小七啊小七,十年太久了,我还没活过十年那么长,再一个十年,那可能就是我的一辈子,我或许回不去了。你我难姐难妹,就不要互相为难了,你别咬我,我给你自由。”
结果这家养的小七,竟寸步不离守着我,偏不走。
我一动,它就要替师父咬我。
这个狗腿子,怪不得师父这么喜欢。
小七是她最喜欢的宝,我只能算二宝。
如今看着小七的尸首,我觉得,它活该。
3
我深知,小七的毒,这小公子是解不了的,我必须去找医仙。
这真是命运推着我走,我不想,却偏不。
但这小公子死倔,我三番五次想逃,都被他捉了回来。
我已经感觉毒性在散发,我头昏脑胀,四肢剧痛,难受死了。
“小公子,你知道医仙吗?无毒不能解,你能将我送去吗?”
小公子配药的手一顿:“不能。”
“可是我要死了,我痛死了!”
小公子默了默:“医仙他,他故了。”
“死了?多久死的?”
哀叹:“今日是头七。”
这么一算,师父让我出发前五日,这老头就已经死了。
果真隔着半座山,这消息也过分不灵通了。
但我又好奇,如此医仙,让我师父愁了大半辈子,是何人杀的。
小公子叹了口气:“吃肉时,噎住了,一口气没上来。”
……
虽然但是,我还是欣喜,不用等十年了,我如今就能回去。
我一激动,差点从木塌上蹦下来。
小公子看着我扭曲的表情,温柔安抚我:“不用担心,我能医治好你。师父走时,留了这蛇解毒的药方。”
“你师父?”
“是的,在下轩子墨,是医仙之徒。”
我愣了,看着小公子的样貌举止,觉得可惜,这么好一个人,竟然是个医。
可惜了。
但我又多了一丝忧虑,师父的敌人是医仙,那他的徒弟是不是也应该除掉。
师父常年教导我,给别人留后路,就是堵死自己的路。
可那是师父的路,与我何干。
头七那日,小公子在院中烧东西,我问他这是干什么,搞得乌烟瘴气的,真难闻。
他说,是给师父烧的,人死了,只有烧了的东西,才能送下去。
就这么些日子,我与小公子一人一间屋,我睡他的,他睡师父的。
康复那日,小公子不在院中,许是上山了,我便独自离去了。
我早就在心里编算好了如何邀功,自己是如何富贵险中求,击败了老医仙。
小七早就回去了,许是不认识路,走丢了。
为了让生活更美好,关于医仙有个徒弟这事儿,我必须扼杀在喉咙里。
但我回到谷中,却发现师父,死了。
4
她是被毒死的。
被自己毒死的。
许是因我离去的时间有些长,她无人试毒,便对自己下了手,奈何没有挺过。
事业心太强,也不是好事。
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毒,但确实是不曾见过的厉害,她周身都已溃烂。
她的血液沾染上我的手臂,便留下了灼热的痛感,她周身的毒气进入我的鼻腔,让我有种濒临死亡的感觉。
我将师父烧了,希望能将她送下去。
看她烧成了灰,我从她屋子里翻出银两,留作念想。
漫无目的,无路可去,不知不知觉又走到了那片山林。
远远又看见那白衣少年在山间采摘采药,忽然心生一计。
他师父死了,我师父也死了,我俩孤男寡女,为什么不可以凑一起干番大事业。
我能制毒,他能解毒,若我们一边放毒,一边卖解药,这……
我这小脑袋瓜,绝!
于是我一头撞在了石头上:“啊,救命!”
那小公子听见了,果真循声而来,他关切地扶起我,看着我头上的大包:“怎么是你?我寻了你几日,以为你离开了,今日怎么又在这,迷路了?”
我扑进他怀里,药草香气淡淡苦涩,衣袍柔软让人安心,抱着真舒服。
他怔住片刻,一抹鼻息噗嗤在我头顶,过了一会儿,手掌轻柔地拍打在我背上:“你家在何处?我送你回去。”
“我没有家了,我家人都死了,死得七窍流血,尸骨无存,惨绝人寰……”
师父说了,这些好人都有软肋,软肋就是听不得人间疾苦,你越苦,他越疼。
拍着我背的手掌半晌才落下:“不论是七窍流血还是尸骨无存,都已无力回天。不如这般,你先随我回去。”
“好啊!”
“对了姑娘,先前走得匆忙,还不知道你姓甚名谁?”
我瞥了一眼地上的土茯苓,随口一说:“胡灵儿。”
又一想,师父没来得及给我取名就死了,真可惜。
5
轩子墨成了我的第二个“师父”。
但我从不叫他师父,也从心底不认为他是我师父。
他只不过比我多活五六年,我俩半斤八两。
好在,他也不强求我如何称呼他。
而后我发现,毒与医其实差别不大,相同的草药名字,都需不断尝试,不停试药。
只是一念之间的分毫之差罢了。
他与师父一样,管我吃喝,教我药理,但却从不让我来试药。
他不知我百毒不侵,我也绝不会提,试药的苦,我不想再吃。
可有一次,他试药后高烧不退,鬼门关里走了一遭。
我这才发现事情的严重。
他和师父一样,是会死的。
可我不会医人,如若他也死了,我往后的计划就打了水漂。
我劝他:“这种事儿你让我就是了,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,我听旁人都这么说,儿子为老子做事,天经地义。”
他有气无力地,竟笑了:“你啊,不必这般讨巧我。”
他当真固执,药碗举得高高的,我从未够着过。
我只能眼巴巴看他喝下,在心里默默祈祷,别死了。
这轩子墨,真是愚蠢。
后来我更发现,他哪里是愚蠢,是愚不可及。
轩子墨平日帮上山求医的村民看病,不取分毫,甚至还担忧他们来去不便,为他们准备吃食。
平日里的生计是靠他精巧的手工编织的各种小动物,在山下售卖而得。
他日子过得素,比起我与师父时,简直算得上清贫。
我受不了,还搭上了师父的银两,为我们改善生活。
而山下那些卖我们东西的人,都是熟悉面孔,在院里哀求时句句真情实感,收起我们的钱时也是,倒真是表里如一。
我觉得我跟他待久了,自己也愚蠢了。
这真可怕。
于是,我与轩子墨说了数次,收诊费药钱,要留下吃饭的,也得给钱。
但轩子墨拒了我的提议,他说他师父在世时,本碌碌无为,却因为镇上越来越多人中毒,有了名号。那时前来看诊的人更多,师父从不收分毫。更何况,最近中毒的人已经无了,前来的人,也越来越少,也算不上负担。
我一边熬着药,一边驳他:“钱很重要,有钱什么都可以买。”
他笑着摇头,面上依旧是平和的:“并未有那么重要。”
我反驳:“你有因为吃不饱当过乞丐吗?”
他眉头皱了皱:“没有。”
但我有。
我爹娘不知怎么地就没了。
那时我尚小,被一个乞丐捡了去。
他要我每日去要钱,要够了才有吃食。后来他死了,我长得大些了,那些人便不再给我钱。我看着白馒头流口水,抢走一个,跑不快被那卖馒头的老头打个半死,死咬的馒头,被扔了。
后来我被一好心的老板收了去。
刷盘洗碗,洗够了,便能有些吃的。
我忘了她是怎么死的,好像是铺子被人抢走,一夜之间,便都不知何处去了。
我又从了无处可去的人,无人待见我,我躲在山脚,被师父捡了去,才过上人的日子。
这小公子虽然生在山林,但那目光看向众人,都是满目的爱,举手投足间像镇上那些读书人,言语里都是不骄不躁。
我真想问他,毒蛇就不值得被爱么?你砍下它头时,可是干脆利落呢。
罢了,何不食肉糜。
他定没有吃过苦,挨过饿,怎么会懂钱是何物。
不能从言语上感化他,我只能从行动上改变他。
他在院中栽种的草药,是他的宝贝,他看着草药的目光,就像我看着钱,满眼都是希望。
于是我连夜将那些草药拔了个一干二净。
他清晨出来,我还在努力,而后我就听见他的惊异。
我故意气他:“太素了,没精气神,我种些花。”
骂我吧,像狂风暴雨般骂我吧,然后我再言传身教,告诉他,一个正常人,如果没有钱立足,就会有失去草药这般的难过。
但他却不曾生气,而是叹口气,上前来,白衣粘泥,为我清理出一片空地,又画出一道泥线。
“这半是你的,种花。另一半,你不许踏足,不许碰,若是碰了,便不许吃肉。”
我要的是那花吗?
不,我是想让他下凡做个食烟火的人。
会因挚爱剥夺而愤怒,因失去而忐忑。
我想要他怨我,好心没好报,再惩罚我,怒斥我,管教我,让我试毒,让我回报弥补。
可他却不怨,还允了我的无理取闹。
师父曾是待我最好的人,她只让我试毒,听话,就给我吃喝和给我买好看的衣服,教我道理。
但如今,有一个人,比师父待我更好了。
我莫名就流下了眼泪:“你这个人不讲道理!”
“我怎么了?”他怔住。
他真的太不讲道理了。
“世上哪有什么付出,就可以讨到好处的道理?你这么对待所有人,就是不讲道理,坏了别人的道儿!他们看病抓药,为什么不给钱,我在这吃喝,惹得你成日不开心,你为何还要留下我?人与人之间,就是要互相索取啊。”
他似乎没料到我会说这些,沉静了好一会儿,开口道:“你腰上那值钱的玉佩,赠予我吧,我向你索取了,你可能安心了。”
啊,这——
那玉佩有毒,如今我并不想毒死他。
“我索取,你又舍不得?那就罢了,往后不许提这些话。”
怎么能不提?
“拿去。”我将玉佩扯下给他。
反正还要十几年才能死呢,那时候,我已经学会他的医术了,有他没他也无所谓。
他盯着那玉佩半晌,宝贝似的擦擦,放进怀里。
我抹去泪偷笑,终于开窍了。
6
我的养成系合伙人,究竟何时能成长为我想要的样子呢,或者我何时能学会他的本领。
日复一日。
我熬着药,遐想着。
我原以为学医不难,后来才发现师父教我的不过皮毛,学医太难,救人比毒死人难太多。
轩子墨长高了不少,有了几分坚硬的气质。
近来前来看病的人多了些。
但大多是女子。
我瞧着她们面色红润得紧,脉象也健康得不行,是害了相思病。
这些我是懂的。
我师父曾喜欢将情情爱爱挂在嘴边,虽然是那样一个毒妇,平日里最爱看的便是爱情话本。死人什么的,她从不落泪,别人砸门,她也从不悲哀,只有看话本,哭成个傻子,是气哭的。
她一边哭一边骂:“会写话本的人都死了么,这都是什么烂故事!穷书生爱上富家小姐就双双赴死。死了也还好,但这女的死了,男的还活着,还高升了!一边妻妾成群,一边饮酒落泪怀念故人,我呸!要我写我就写女子夫君成群,再不济,霸道王爷爱上我,或者,穷书生爱上第一毒师,爱而不得,书生求毒寻一死。”
那时候,我觉得师父是有些才华的。
如果不做毒师,写话本许也能成个角儿。
我在内熬药,看着院子里的小娘子,就像话本里写着那般。小娘子个个锦衣玉食,脸上的脂粉味儿熏人,就是手脚脑子都不大好。一会儿丢个荷包,一会儿簪子落下。
想着我就来气。
将荷包、簪子,乱七八糟的东西拿起,我出去,将每个东西都绑在了小娘子的身上:“我给你们做了绳,绑身上,不会掉了。”
小娘子们面色不太好,还是道谢离去了,院子中又安静了下来,就剩了几个人。
一个染了风寒瘦骨嶙峋,一个看着强壮与母亲一道,还有几个毛病轻的。
我本以为墨子轩会说我“胡闹”,簪子怎么能系在人身上。
没想到他竟笑了,又忽而严肃:“灵儿,去将药端来给。”
我去给病人们端药。
轩子墨闲下来,他又在编那些小动物,我进屋时,瞧见他编了好些小鸟。
“师父教我医术以来,我的第一位病患,便只是小鸟。”他注视着手里的活儿,白衣侧影仿佛神明造物,“那时我目光短浅,便以为自己操控了万物生死,如今想来,万分稚嫩。”
我看着他,似乎有些明白那些小娘子为何次次落下东西。
我心道,加上我,万物的生与死,我们便能操控了。
正在这时,咔嚓——
院中传来异响。
我和轩子墨匆匆向院外走去。
只见那个同母亲一道来的男人手中药碗落地,于院中,在众目睽睽下死去了。
大惊失色。
轩子墨被那几人围住。
随那人前来的母亲在院中撒泼,开始了对轩子墨的讨伐。
“我儿怎么喝药就给喝没了?你还我儿子命!”
“庸医!还命!”
这事儿太突然了。
轩子墨苍白无力地解释:“让我去探探脉象。”
那些人哪里听得进去,紧紧拽住轩子墨,不让他再触碰那尸首分毫。
我坐在门沿边,心里有些复杂。
不久后,村长便来了。
村长在门外,客客气气。
“轩先生,您把我们村里的人害死了,这事儿躲不过去。二壮是张婶家唯一的根呀,这是给人断了后。不过我也劝了张婶,我们和善解决,你赔些银子就好。”
我坐不住,和他们理论:“我们救人分文不取,救了多少人怎不见你们来报恩呢。如今就死了一个人,还要我们赔钱?”
轩子墨将我拉到身后:“你去屋内呆着。”
我不。
这群人会吃了轩子墨的。
只见,轩子墨从衣侧拿出绣花布袋,是我闲着无聊时绣着玩的,虽然很丑,但他不嫌。
布袋里应当只有些他的散碎银两,他将银两分文不剩地递给了村长。
气死我得了!
更气人的是——
“这也太少了吧!”
“轩先生难倒觉得人命只值这些银两么?”
“我瞧着那玉佩也不错,玉佩也……”
有人伸手真就去取那玉佩。
快抢快抢,毒死他们!
却没料想,轩子墨竟然一收手:“这玉佩,不行。”
被驴踢的脑子都比这好使!
我再不开口,恐怕就要和他一起倾家荡产了!
我冲上前,指着撒泼的女人骂:“给你银子,你儿子就能活过来吗?既然给银子也活不过来,那你还回来!”
但下一秒,我就被轩子墨拉到了身后。
医者施针如此沉稳的手,抖得及其厉害。
“胡闹,你进去!”
他很用力地,推了我一把,将我推向屋内。
“你才胡闹!”
“你给我进去!”
他推我更使劲儿了,是真的很生气。
我愤愤不平地进了屋。
他从没有对我这么凶过。
我拔了他的草药,他都没有生我的气,可今天却因为一个陌生的死人与我生气。
况且那人没病没灾,就是蹭吃蹭喝。
轩子墨也知道,每日开的药都是强身健体,未说破。
这种占便宜的人,难道不该死吗?报应罢了!
我把门关死了。
一个字我都不想听见!
但我还是听见银子响动的声音,还有搬动院子中杂物的声音。
我气得扑再床上大哭。
比我师父看话本时还生气。
师父说,好人一般都没有好下场,因为他们的心太软了,谁都舍不得伤害,只能伤害自己。
7
这件事,虽然轩子墨认怂,息事宁人。
但也因祸得福,这小院终于是清静了。
再也没有人来山上寻轩子墨看病。
这就对了,镇上明明有大夫,只是要钱罢了。
这些人,为了那几个钱,能爬几里山路,说明这病也不是很严重嘛。
若是真严重的,床都下不了才是,还爬山?
悠哉,悠哉。
我在山间捕鸟。
他在院中看医书。
我偷摸着用鸟试毒,鸟死了,我又捕鸟。
他在院中配草药,用自己试药。
我将毒方记在秘密的小本子里。
他在院中记下新药方。
我还将那后院拓了出去,种上了些瓜果吃食,但也给他留了一小块种药的地儿。
他为我梳头,越发顺手。
我绣着香囊,放进草药,针线也不再扎手。
香囊上绣了一株夹竹桃,虽然有些歪歪扭扭,旁人认不出,但我知道。
师父院中就有一株夹竹桃,制毒时常会用到。
院中的花开了,色彩斑斓,生机勃勃。
多美好啊。
我脑中已经有了那幅蓝图,我制毒来他配药,我放毒来,他卖药,我们盆满钵满把家还。
我看他将药房誊抄在好几个本子上,工工整整。
好奇:“你有爹娘,怎么会成医仙的徒弟。”
他顿了顿:“师父就是我的爹。”
“那为何你称他师父,不唤他爹。”
“他教我药理,是师父,但从不教我为人,便不唤为爹。”
我不懂,也懒得懂。
“那你娘呢?”
“他们和离了。”
“为何和离?两个人待在一起,不比一个人强么?”
他笑:“你怎这般好奇。”
“我没有爹娘当然好奇,你不愿说算了。”
我拨弄着手里的果子,准备出去逗小鸟。
他瞧见了,似在回忆什么:“年幼时,我常用这果子果腹,却不知怎会有人将毒下在山间的野果中,后来我发了几日高烧。你也小心些,不要乱吃山林间的东西。”
啊,这,巧了是不。
转移话题——
“如今没人再来看病,配药给谁呢?”
他继续誊抄着:“给镇上的郎中,药铺,行医者。”
“这些药方能卖不少钱吧。”
他笑着看我:“我何时说要拿去卖钱,救人命的东西,多一人知晓,便少一人离去。”
我傻了。
我低估了他“爱苍生”的心。
这是什么该死的菩萨心肠。
他竟然连药方的钱都舍不得挣。
若是我坦白自己的身份,告知他我的完美计划,他定会被吓得花容失色。
我突然忧愁了,跟着他,我还有前途吗?
如果我师父在天之灵瞧见我如今治病救人,无善不做,定能气得诈尸。
好在,我将她烧得干干净净,一块完整的骨头都没有。
但是我还是在心中,对着师父已经不知在哪里的骨灰许愿,求求您显灵,给这一根筋开开窍吧。
没想到,师父变成灰也还爱护我,真顺了我的意。
8
山林与村庄长时间没有落雨。
没有落雨,水便匮乏,花死了,草药也不行了,小院后的吃食也快弹尽粮绝。
整个山林都变得寂静。
葱郁山林变得干瘪,以至于后来,我的小菜园也近乎是荒废了。
没了存粮,我与他便要下山讨。
朝廷下拨了赈灾粮食,分发给各户。
每人都会领到,却唯独不给我们,他们看着我们便让道,指着我们的鼻子骂道:“庸医!”
这骂声比以往更胜。
但明明那件事已经过去许久了。
“吃了你的药,没几天,我丈夫便走了!”
“我妻儿也是这般!”
“我老丈人也是!”
“你这哪里是药,分明是要毒死我们啊!”
我与他都茫然,已经许久没有人找他看病了,怎会埋怨他害死人?
“不是你给医馆郎中的药方?医馆都告诉我们了,当真以为你是好心,却没想到给的是害人命的药方,你这是要报复我们啊!”
路人的声音渐大。
“这不可能,我都试过。”他无措地反击着。
我拉着他朝前走,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大旱之时,患病者不少。
轩子墨坐不住,便要赠药方予山下医馆。
山下十几家医馆,他先前誊抄了几分不够。
他抄,我送,也顺便在镇上有钱人家处讨些吃食。
我嘴甜,他们并不拒我,但提起轩子墨,大家还是避讳。
所以这山,我下,比他去强。
那时,我瞧见那几位郎中笑的脸都咧到了耳后,也随便聊了几句,都是半罐子水,闭着眼医人。
只是我上次下山,是几日前,明明都还没这么夸张。
我笃定:“是他们治不好人,赖你身上。可是现在怎么办,我们领不到粮食,他们不会给我们的。”
他皱紧了眉,而后又牵起我的手:“去集市吧,买些粮。”
我一言不发地跟在他身旁,什么都没再说。
他时不时转头看我,似乎是怕我丢了,可我明明攥着他的手。
集市上,现在都是高价粮,赶上大旱,能吃的东西,比金银还贵。
他荷包那几两碎银买不到什么。
我的小金库早就花得差不多了。
我们俩穷鬼,还背负着骂名。
好像是死了不少人,连我也一并骂了起来。
他眼眶有些红润,却还是坚挺着。
他长得更高了,将我笼罩住,似不想让我听见那些闲言碎语。
他明明想落泪,却有泪不轻弹,还摸摸我的头安慰我。
摸头并不能安慰我。
我不是那些傻不愣登的小娘子。
钱和穷书生,我选钱。
“轩哥哥,要不你把我卖了吧,我如今不是小孩子了,卖给有钱人家做个丫鬟,我也有几分姿色,能做个小妾更成。”
他怔了半晌,看向我,将我的手攥得紧了些:“我怎会将你卖了,你不要胡闹。”
“可是,跟着你,我吃不饱。”
这是我第一次跟他说实话。
我看见他手臂青筋鼓成一条线,生气了。
我骗他的话总是甜的,他爱听。
师父说的没错,没人爱听实话。
但他却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:“我会想办法的。”
“你有什么办法?能变出钱吗?能让那些人给我们粮食吗?你是个大好人,但像你这样的大好人,吃不饱。”
“我——”他回答不出来,因为我每个字都有道理。
我松开他的手。
“你如果不忍心,背过身去,不要看我,直接往山上走。等我卖了钱,钱给你,你多买些药材吃食,我也过上好日子。”
他不说话。
我当他默认了。
我伸出手:“玉佩,可以还给我吗?那是我唯一最值钱的东西了。”
虽然现在,这玉佩,一袋米都换不着。
他看着我,一动不动,目光灼灼,似有千言万语。
那白衣依旧,我忽地觉得,话本中的仙,大抵就长这样。
但仙不吃饭,人要吃。
我有些不耐烦了:“给我,玉佩!”
“不。”
他第一次这么坦然地拒绝我,我一愣。
他转身,避开我的目光,向人群中走去,在众人的目光中,大声道——
“我的药方不曾有错,若有病害无法医治者,可送来,让我医治。若是医者不成,我以命相还!”
众人窃窃私语。
我猛地跑过去,拉他,这说的什么鬼话。
他不动,继续说:“若是医治成功,按照市价,你们给我银两,若没有银两,那便用吃食来抵!”
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手从他的衣袖滑落,又被他的大手攥住。
人群沉默着,从未有一刻这般安静。
在这片沉默中,突然有人喊道——
“我答应你!”
9
那个大胆发言的人,是镇上一家有钱人的少公子。
我见过他。
也是前几次下山时,路过他家讨了些水喝。
大旱年间,他家粮库倒是丰裕,就连那水桶里的水,都是清澈诱人的。
少公子的爹心好,带我进去看水桶,炫耀他的财富。
他爹让我随便喝,我便也不客气。
他爹笑看我,沾着可以喝的水,擦去我脸上的泥。
“可惜了,这般小脸,被泥盖住了。”
我也觉得可惜,这么多好好的水,被糟蹋了。
“这大旱不知何时过去,你瞧,死了多少人。如今粮比金贵,多少人将小女娘送老夫榻上,只讨一袋粮。若是你来,老夫给你两袋。”
我看着他爹半只腿都快踏进棺材了。
要是以往的脾气,我早就毒死他了,但如今不比往昔,山上还有个嗷嗷待哺的轩子墨。
我迂回,将辛辛苦苦做的香囊送给他,讨了他片刻欢心,临走时,他还给了我小半袋粮。
但这事儿,我没给轩子墨说。
他那榆木脑袋,不会懂。
没想到,这次下山,少公子的老爹便病了。
要我说,就是小姑娘吃多了,艳福太深,吃不消。
他下不得床,高烧不退,身上还长出些许麻点。
为了方便医治,少公子将我们安顿在客房中。
镇上的人都好奇,打赌是轩子墨是活着出来,还是尸首而去。
我替轩子墨打着下手,轩子墨望闻问切,但那老头已说不出什么话了。
购买专栏解锁剩余48%